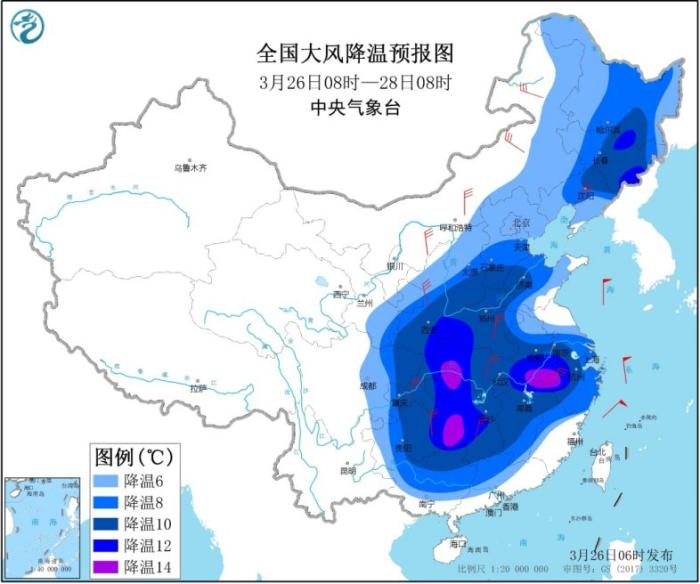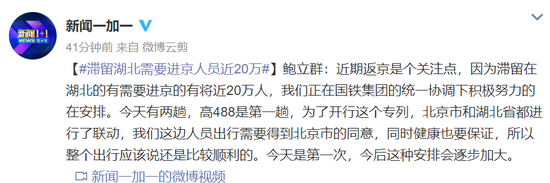月经贫困普遍存在
- 来源:中国青年报
- 时间:2020-09-30 16:44:03
半边天空的隐秘心事
1985年10月1日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》开始实施。第九条只有7个字:继承权男女平等。同一年,福建泉州一家工厂开动来自台湾的机器,生产出第一片雪白的卫生巾。工人们放鞭炮庆祝,红色的碎屑落在红泥路上。
此后数年间,机器一天的生产量,企业的销售员要一个月才卖得完。在当时的中国,绝大多数经期妇女还习惯使用月经带、布料、草纸等。
2020年的某一天,一个漂亮姑娘把6杯粉红色液体倒在一片卫生巾上,再用剪刀剪开,验证吸水后的厚度,然后对着镜头说:“真有你的!”这条微博视频有12.1万次观看。
这是一个早就无人见怪的场景。电视广告、电商平台、超市货架都在传达一个信息:卫生巾有很多品种可以选。
“我国卫生巾真的贵吗?”知乎网站的问答下,有3000多名网友分享买卫生巾的经历。这些声音淹没在“种草”“安利”顶级产品的吆喝声中,就连许多卫生巾行业从业者都没有注意过。
“那个东西很贵”
许敏不知道母亲卖了多少玉米和蔬菜、多少次和人开口借了钱,才保证小女儿初中3年有卫生巾用。
1999年的一天,刚上初中的许敏和同村一位学姐躲进学校厕所隔间,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音量交流。学姐拿着一片白色、没有护翼的卫生巾,指了指背面说:“贴到内裤上。”这是许敏使用的第一片卫生巾。
如今她34岁,在中国市场占有量最大的卫生巾生产企业担任车间组长。这家企业所有品牌的卫生巾,每年销售额约80亿元人民币。
许敏已经不记得,第一次用的那白色的一小片是什么品牌、什么包装。但她清楚记得价格,5元钱13片。许敏的父亲和姐姐常年在外打工,母亲在家干农活照顾她和弟弟,生活费用靠几亩庄稼的收成。在当时,5元对这个贵州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
“好用吗?”母亲问女儿。
“老师让用的当然好用。”体育课间隙,女老师会叮嘱女同学,发现身体“不干净”,要使用卫生巾,并及时更换。有时许敏舍不得,也用草纸。
母亲接下来说的话让许敏很惊讶,“帮我买一包吧”。
她回忆,经期的母亲似乎用布,但那块布从未出现过,不知道被藏在哪个角落。她理解这种心理,出于羞涩,自己也把内衣内裤藏在外衣下晾晒。
她到小卖部买卫生巾,看不懂品牌,分不清包装上的“日用”和“夜用”。她的眼神只在数量和标价上游走。
女儿为母亲买回了第一包卫生巾。“4小时要更换一次”“要贴在内裤上。”许敏复述老师的话。
后来有天晚上,她正值经期,坐在板凳上写作业,忍不住对母亲抱怨:“好麻烦,到处都是血。”母亲安慰她:“这是每个女人都要经历的。”
在当代大部分卫生巾广告中,作为模特的少女总是行动自如、笑逐颜开,宣传使用某产品会“舒服自在”。早在1930年,上海《妇女杂志》也以解放妇女、舒服自由为广告推荐一款用纱布和棉花制作的进口卫生巾:一面无吸水性,不至于外泄,一面吸水性极大,“何等的适意吓”。
一名为多家卫生巾企业做品牌策划的业内人说,年长的女性对于卫生巾品牌的忠诚度高,不会轻易更换品牌,因此,大多数卫生巾广告会选择年轻的代言人,吸引少女购买。2015年新广告法实施前,一些男明星也以“大姨父”“好朋友”的形象出现在卫生巾广告里。
当许敏再次和母亲要钱买卫生巾时,母亲说出了难处,“那个东西很贵”。为了能让小女儿用上卫生巾,母亲出门去和邻居借钱。有时候,许敏也会问母亲,“用完了没有”,答案几乎都是还没用完。
许多人在互联网中写下自己的经历:有女孩拿到卫生巾也不会用,只会用布条;病重的中年女性想省点钱买散装卫生巾。也有网友说,工作后最开心的,是实现卫生巾自由,想用最好的卫生巾,不想再委屈自己。
初中毕业后,许敏离开贵州老家,到福建打工。她的双手在罐头厂洗过鲍鱼,在鞋厂刷过鞋底的胶水。成为母亲后,她到了卫生巾企业。
最初在生产车间,她是流水线的产品包装员,每一包卫生巾只在她手里停留3秒钟。她坐在塑料椅上,每天工作11个小时,重复同一个动作:双手捏住包装袋的两侧,右脚踩一下踏板,机器将卫生巾包装封口。长期的劳作使她右手中指有些变形。
她将完成封口的卫生巾放回传送带。这些外包装印着卡通形象的卫生巾会进入纸箱,通过货车送往全国各地的超市和小卖部,包括她的贵州老家。她自己也用,过年回家,她还把卫生巾送给亲戚朋友。
11年前的一天,许敏打电话告诉母亲,自己有了一份新工作。母亲说:“那是不是有用不完的卫生巾!”
老板们都想做高端产品
那看上去像一团团棉花,雪白轻盈地飘在传送带上。只有六分之一头发粗的纤维层层叠叠地交织在一起,成为卫生巾最贴近皮肤的表层。
早期卫生巾生产工艺传入中国时,绵柔质感的无纺布能保证卫生巾表面干爽透水,是工厂采购材料的首选。直到最近几年,棉花、蚕丝、竹纤维等材料制作的表层才进入市场。
“做面膜的蚕丝都用上了。”经营一家卫生巾代加工企业的林佳感慨,为了让女性有更好的使用体验,制作卫生巾亲肤层的材料越来越昂贵。
林佳1980年出生,她使用卫生巾的最初体验是:屁股疼。此外她还能说出一大串,包括太厚、闷热、背胶粘不牢、用久了会褶皱等,这些都和早期卫生巾的生产工艺有关。
林佳的母亲一直使用月经带,在女儿初潮时,她摸索着教女儿:在内裤上贴上卫生巾,再在卫生巾上垫几层纸。有一天林佳自己悟了,母亲是为了节省。
社交媒体中,网友分享着与母亲有关的卫生巾故事:内裤太旧,松松垮垮,卫生巾贴上去不管用;使用母亲收藏多年、背胶硬化的卫生巾,自己再贴点双面胶固定。
林佳工作后,改用进口品牌,因为广告写着“不侧漏”,她可以不用再用力搓洗掉内裤上的血迹。
新一代女性的需求推动了卫生巾生产技术的进步。最明显的变化是,卫生巾开始加上两片护翼,可以翻折到内裤外侧固定,防止经血漏出。
林佳继承父亲的事业后,长期为国外品牌代加工卫生巾。林佳和外籍客户吃饭时,把最新款产品都摆上桌来介绍,有一次餐馆女服务员看到满桌子卫生巾,吓了一跳。
她回忆,最近几年,经营卫生巾企业的老板们每次聚在一起,讨论的是消费升级,做出高端产品,包括研究更高级的表层材料。
“你把它想象成一个三明治”,林健熟练地撕开一片卫生巾的边缘,最贴近皮肤的表层和贴有背胶的隔离层是三明治的两片面包,中间夹着的吸水层承担了卫生巾的主要功能。
这位生产班长把那片卫生巾立起来,抖了抖,像细盐一样雪白细腻的高分子吸水树脂掉落在他的手掌上。它们吸水后会变成有弹性的透明小球。
入行12年的林健,生产过至少十几亿片卫生巾。他所操作的机器有15米长,每分钟生产780片275毫米长度的卫生巾。他工作最大的成就感来源是,去超市时,拿起一包卫生巾,防伪码会显露这包卫生巾是经他手生产。
林健回忆,过去由人工检测污点、护翼折损、表层花纹偏移等问题。眼下,影像仪器自动检测后,会将次等品挑出,扔进次品框里。
人工包装的工作也逐渐被机器代替。在线称重装置能精准数出10片卫生巾,装入包装袋里封口,机械抓手一次抓取8包卫生巾放入纸箱,3次抓取后,纸箱会被封上胶带,经传送带运走。这些工作以往由一条产线两侧坐着的约20个女工完成。
这和1985年许自淡生产第一片卫生巾的场景不同。红泥地上的鞭炮声响起后,他参与生产最大的期望是,降低废品率。
35年后,在办公室里,这位恒安集团女性健康产业发展部总裁兴奋地拿起笔,在白板上画出1985年那片卫生巾的横截面,“无纺布、两层卫生纸、木浆、卫生纸、隔离薄膜”,有6层。那时候,高分子吸水树脂还没有进入国内卫生巾生产工艺中。
假货为何畅销
从外包装看,这包卫生巾和官方渠道售卖的“佳期”卫生巾没有任何差异:20年不变的设计曾被消费者批评“老龄化”“老土”,包装上印着生产日期和“合格”字样。它被装进一个写着“多顺畅卫生床垫”的纸箱里,送到云南省某批发市场,等待小卖部老板进货时,以低于零售价10%的价格卖出。
它是假货,来自一个仅有一台生产机器的小作坊。在那里,一摞摞仿造“佳期”品牌的包装纸塞在麻布袋里,墙面污浊,地面散落垃圾、废料。当警察和企业的工作人员赶到,造假团伙已经逃走,留下一地包装纸和等待售出的成品。
在中国一些偏远地区,佳期卫生巾吸引中低收入人群。市场经理缪一豪回忆,这一类制假售假事件,他们平均每年要处理3次。
此外,仿冒其他品牌的侵权产品也让他们感到头疼。字母近似“ABC”品牌的“ADE”、名字类似“七度空间”的“八度空间”等,会在购买力并不高的地区和“佳期”争夺市场,价格只有竞争对手的一半。
这部分市场大多集中在城乡接合部、山区或少数民族聚居地。缪一豪认为,这些购买仿冒、侵权商品的女性不会轻易地改变消费习惯,不会去购买价格偏高的品牌产品,因为她们“哪家便宜就用哪家,可以不用就不用”。
这些需要低价卫生巾的女性,处于长期“失语”的状态。林佳发现其中有一道难解的题:企业都更愿意拼高端,不愿意生产平价卫生巾,然而一部分女性消费能力有限,无法承担品牌卫生巾的费用。
在全世界范围内,月经贫困普遍存在。在非洲,有些贫穷女性不得不出卖身体,换回购买卫生巾的钱。在英国,每年有13.7万女孩因买不起卫生用品辍学。
在生产第一片卫生巾前,18岁的许自淡不知道卫生巾是什么,只知道这份工作是往机器上挂材料,每天能赚2.5元。老板教他,女人来例假的时候,用卫生巾比较方便干净,不用洗月经带。
同学聚会上,有人说错了卫生巾和餐巾纸,他学着老板的话跟对方解释。有同学取笑他,“大男人怎么想去做那个”,他说这是我的职业。
他极少有害羞的时候。在车间干活,额头冒汗,他把制作卫生巾的无纺布塞在帽子下吸汗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,他到江西销售卫生巾。小卖部的年轻姑娘一听“卫生巾”,不应答。年长的老板娘问“小伙子你为什么来卖这个”,他答,“个人职业,我已经做了10年了”。
因为与性征、生育、隐私处密切相关,这种女性特有的生理现象有很多遮掩的名字。中国人的暗语是“倒霉了” “来事儿了”,荷兰人爱说“红色的法拉利来了”。西班牙人说,“西红柿掉了”。法国女人则说,“英国登陆了”。
它似乎不是一个能公开讨论的话题,在两性之间有着更深的隔阂。当年在教室里,许敏可以大声说出“来亲戚了”,因为男同学听不懂。贵州老家农村的老人,偶尔会提醒少女,别人家办喜事,女孩子身体不干净,不能去别人家的客厅。
2002年,已过六旬的奶奶听说朱丽敏要制作卫生巾,问她,“那东西怎么吸收?为什么不会漏?”亲戚问朱丽敏的职业,她回“生活用品”,遇到追问时,她憋着不敢说出“卫生巾”三个字。如今,她当上了车间组长。
时代不同了。林佳的儿子上小学五年级时,把母亲企业生产的卫生巾送给女同学,还计划帮老妈把广告贴在高铁座位的背面。
许自淡开车接送女性客户时,对方主动索要卫生巾,他能马上掏出一片产品请对方试用。他曾把清凉型卫生巾送给女儿的同学,小姑娘第二天说:“叔叔你坑我,半夜我冷醒了。”
关于女性经期受激素水平影响情绪波动的知识在公众中普及。许敏大嗓门,爱唠叨,老公抱怨:“你大姨妈来了吗,口气那么冲!”正在经历青春期的女儿跟着大笑。一些男士会在公开场合调侃,自己来了“大姨父”,心情不好。
然而,提及少女时代的往事,许敏却希望不要透露真实姓名,仿佛那是一段不可言说的秘密。
她清楚自己的职业“天花板”
在恒安,许自淡曾研发一款有中凸设计的卫生巾,凸起的部分能更贴合女性私处的构造。为此,他专门咨询妇科医生,了解女性私处的特点,把一片卫生巾中凸部分的长度、宽度、厚度逐项确定,再把试用品分发给女同事,请她们分享体验。
“中国女人的屁股越来越刁。”最明显的变化是,同样粗糙的材料,早期女性选择忍受,而如今会投诉。
供需关系变换推动了产品提升。许自淡回忆,上世纪90年代初期,卫生巾需求上涨以后,许多超市、小卖部的老板开车来工厂门口排队,每次至少拉两车以上的卫生巾。到了1998年,国内陆续成立更多卫生巾工厂,产量提高,他的卫生巾不得不开始促销。
外资企业的进驻也冲击了国内卫生巾品牌的发展。同样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,外资企业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,与国产卫生巾品牌争夺一二线城市的超市货架位置。
恒安集团卫生巾品类总监金蓓蓓介绍,如今,一二线城市购买国外品牌的女性更多,而国内品牌在三四线城市市场占有率更高。双方的优势在于,跨国品牌擅长营销宣传,侧重讲述品牌故事,而国内品牌线下的销售渠道覆盖面积更广,产品布局兼顾中高端市场和消费力有限的人群。
比如,曾经定位中高端市场的“安尔乐”,眼下更为中年妇女、95后的小镇青年青睐。
近20年来,中国卫生巾市场扩大,产能逐年提高,但卫生巾单片价格每年上涨。佳期市场经理缪一豪明显感觉,由于线上渠道抢走一部分线下市场,一些实体店铺为了生存,对供应商的收费越来越高,抬高了卫生巾的价格。
另一个因素是广告。与同样在上世纪90年代创立的其他国内品牌相比,佳期卫生巾没有及时在细分领域中找到位置,价格涨速慢,目标消费者逐渐迁移至中低收入群体。相比而言,其他一线品牌对产品创新投入大量广告,打开知名度,价格也相应提高。
福建省卫生用品商会执行秘书长郭惠斌介绍,2006年,福建省泉州市的卫生巾企业数量达到峰值,接近400家。还有不少企业负责研发制作卫生巾的机械和材料。此后经过多次“洗牌”,生产低品质卫生巾的企业被淘汰出局。
而活下来的中小企业,找到的出路是依赖外贸,为微商、电商、直播的商家提供代加工服务,追求差异化产品。
潘儒愿从父亲手里接过一家卫生巾生产企业。父亲留给他的经验是,做创新型产品,服务高端人群。近5年,他的企业接到内裤被卫生巾背胶撕破的投诉变多,询问后发现,越来越多女性不再穿棉质内裤,而选用真丝内裤等。他不得不重新调整卫生巾的背胶的宽度以及胶力,保证粘得稳,又不会撕破新材质的内裤。
一个卫生巾生产企业的销售人员介绍,他们每年生产约1亿片卫生巾,约七成生产力是为100多个微商提供代加工服务。商家可以根据目标消费者的定位,用不同质地的材料和包装,私人定制最合适的卫生巾。光是卫生巾中间那条抗菌芯片,就有负离子芯片、甲壳素芯片、暖宫芯片、中药复合芯片等各种名头。
朱丽敏是泉州市晋江市安海镇人,去恒安上班只需要骑15分钟摩托车。她总不愿意休年假,希望能为两个儿子各攒一套房。许敏的老公是电焊工,夫妻俩把一对儿女从贵州带来福建上学。
这两个女人如今都是车间组长。朱丽敏清晰地知道她的职业天花板,“我初中毕业就只能到这了,没法往上。”她指的往上,是坐在办公室里做管理工作。
贴在工厂外的招聘简章上,清楚地标明了自动化生产线的员工需求:设备技术员要求男性,中专以上学历,负责自动化产线操作维护和简单维修;产品包装员要求女性,学历不限,负责产品包装。只有设备技术员列明了明确的晋升机制。
在这个满足女性刚需的产业里,男性参与了多个环节。恒安集团上世纪80年代的卫生巾销售员都是男性。福建省卫生用品商会的会刊里,大多数介绍企业发展的文章旁,配有男性领导的照片。一家代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里,一位两鬓花白的男士,把眼睛贴近一片卫生巾检查产品质量。
在供大于求的行业背景下,仍有隐秘的角落。
2020年9月,云南昭通市一所山区小学附近的小卖部里,老板娘向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秘书长张茹玮介绍,卖得最好的一款卫生巾售价5元,有30片。张茹玮撕开外包装,每片卫生巾没有独立包装,背后的离型纸印着不同品牌的商标。
张茹玮记得重庆山区一个生长在单亲家庭的小女孩。母亲出走了,父亲带她长大,她不好意思开口索要十几元买卫生巾。
在云南昭通,几个女孩面对爱小丫基金的工作人员的镜头,笑着说出她们的难处,“我没有穿小内裤,穿起来我不习惯”“没有人告诉我穿内裤的好处”。
一个网友评论,“真正的文明应该是,社会对底端及无法跟上时代脚步一类人的宽容”。
(应受访者要求,许敏,林佳为化名)